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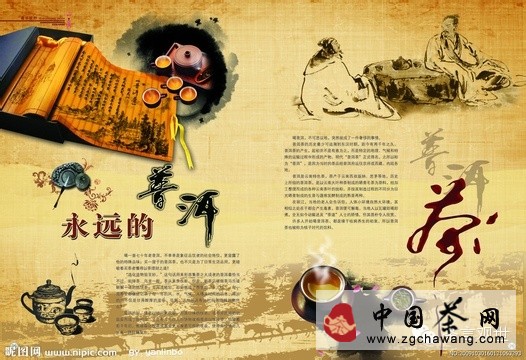
今天是甲午年正月二十,吃完晚飯,看看時間還早,就想著坐下來寫點東西。其實一直都想寫的,只是每每動筆的時候,看看窗外林立的煙囪廠房,就壞了我的心情。前兩天,本遇上了一次難得的茶會,而且那天下了立春以來的第一場雪,心里想這下有靈感了,可是當我站在窗前,一眼望去那灰蒙蒙的廠區,遠處傳來機器的轟鳴聲不絕于耳,從樓上往下看連只貓都沒有的蒼涼感不覺油然而生,算了,沒心情,不寫了。但是今天,的確想寫一寫了。
算來從去年七月開始學喝茶,至今已有半年有余。為什么說是“學喝茶”?那是因為以前喝茶一直很不講究,只要是茶,喝喝而已。但又不能說是“學茶”,因為歷經半年,我認為學茶的境界要求太高,是要作系統研究的,我遠沒有達到。而我這半年來只是較為迷戀普洱而已,并未過多涉及其他茶類,所以愈加只能說是“學喝茶“了。

初識普洱茶對我來說非常偶然,無非是一片虎年冰島惹出的故事,這在我以前的《茶緣》里講述過。從那以后我喝過一些茶,也買過一些茶,當然,更多的是也蹭過一些茶。有幸結識了段老師、魏老師、秦總、樂府三爺等資深茶人,對我的幫助頗大,使得我的品茶水平和對茶的認識有了較大的提高。剛開始只是接觸一些新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接觸到了熟茶、有一定年份的生茶和熟茶,在喝茶的過程中也偶爾翻閱了一些資料,初步得到一些認識。但依然對有些問題存在疑惑。
首先,是關于普洱茶的定義。是否必須是云南省境內瀾滄江流域的大葉種曬青毛茶才能用作普洱茶的原料?我們都知道,古時的六大茶山(易武、倚邦、攸樂(基諾)、漫撒、蠻磚和革登)其實范圍很是有限,而今茶區的范圍已經擴大到版納、普洱、臨滄甚至保山等地。那么,緬甸臨近云南的茶青,如果采用普洱工藝,能不能也歸為同一類?我國其他地區的品性類同的大葉種茶青,是否也可以用同樣的工藝制成普洱茶?而且在傳統茶區內也有用中小葉種制茶的,這些難道就不是普洱茶了嗎?
其次,是關于普洱茶的工藝。我們知道普洱茶的工藝流程要求的是輕殺青,輕揉捻,是以曬青毛茶為原料制成。這主要是為了有利于茶的后期陳化,讓茶的內含物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轉化體現出來,以達到愈陳愈香的效果。但是規模化的生產,機械化的流程,曬青場地的限制,一味追求當年新茶的口感等等,現在這一工藝還能被堅持下來嗎?如果不能,那些重揉捻,高溫提香,采用烘青工藝的茶還能不能被稱之為普洱茶?
再者,是關于普洱熟茶問題。我們都知道,在1973年以前是沒有普洱熟茶的,而且,普洱茶被稱之為“可入口的古董”。也就是說,普洱茶應當有一個漫長的后期陳化的過程,所謂“三分制,七分倉”,良好的的倉儲存放對普洱茶完成后期轉化非常重要,這一過程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完成的,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種慢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么,人為地快速渥堆發酵來縮短這一過程,對茶品的性質有沒有破壞?用這種類似于“拔苗助長”的所謂工藝制作出來的茶還能不能被稱之為普洱茶?這些熟茶經過長期存放是否也能達到愈陳愈香的效果呢?

另外有很多問題,在這里我不想一一列出,留在今后喝茶的過程中慢慢解惑,也好為我自己繼續學習喝茶保持一點動力。而且有些問題的提出,我本人并不是一定要有個非常準確的答案。只是寫一點勉強可以稱之為文字的東西,來證明一下自己還是在用心喝茶,希望老師們不要對我過于失望而已,我的確是慚愧之至了。